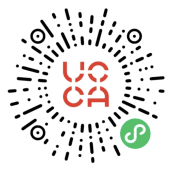UCCA北京“现代主义漫步”展览系列对话
2024.1.7
“现代主义漫步”展览系列对话
寓言的赋格:保罗·克利与包豪斯
2024.1.7
14:00-16:00
欧洲的艺术先锋派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高潮,其变革已远不限于风格演化和题材更替的层面,艺术既定的范畴、审美体制、创作方法乃至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冲击。一旦艺术回归社会生活的呼声成为这场运动的主音,架上绘画就不可避免被卷入风暴的中心。架上绘画的整个传统尽管自19世纪后半叶就经历着重重变革,但时值总体战争的爆发,这种“传统”艺术行为才终于激化为剧烈的自我否定。同时代先锋派运动诞生的各类新的创造活动,也仿佛在宣告架上绘画的死亡。旧世界业已崩解,新世界尚未结体,恰恰在这样一段历史间隙中,画家释放出强烈的构型冲动,要为异乎寻常的存在状况和精神体验给出表达形式。这是马列维奇和蒙德里安所处的情境,也是保罗·克利和康定斯基所处的情境。于是人们看到,架上绘画在他们那里似乎以某种与传统断裂的方式重新发端,也因此从根本上改变了后世的绘画经验。
然而,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,那样的时刻,对于绘画究竟意味着幸或不幸?有人赞叹那几个世代的艺术家中最伟大者让绘画得以重生,也有人抱怨正是那种断裂式的变革把绘画引向穷途末路。引发的惊叹和困惑,不知哪个更多。诗人波德莱尔曾对画家马奈直言:“你是你们艺术的最后一人也是第一人。你们这个腐败堕落、濒临死亡的艺术,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。”将近一个世纪之后,哲学家梅洛-庞蒂却接着保罗·克利的墓志铭宣称,“世界在持续几百万年之后如果还存在的话,对于画家来说,它仍然有待去画出,世界将在没有被画出中毁灭。”绘画自身的生灭不再成为其问题,才让人们有可能这样重新发问:如果绘画行为终究不能灭除,就像写作行为终究不能灭除一样,那么保罗·克利这样的画家有可能为我们做出了什么示范?
这一问题语境给本场讲座定下基调。一个公认的事实是,保罗·克利创作生涯的巅峰阶段正好与他在包豪斯任教的时期基本重合。但他的包豪斯教学与其个人艺术创作究竟在什么程度上、以什么方式相互作用,研究者们对此仍莫衷一是。本次讲座以“寓言的赋格”为题,在分析克利作品和教学草图的同时,也会试着回应这项议题。我们将看到,克利独特的连接现实与抽象的思维模式,如何经由这段时期快速走向成熟:他如何借助教学为他的艺术创作打开理论反思通道;他如何接收来自包豪斯内外的冲突力量,借助异己的力量系统化他最关心的问题——事物的生成过程;他的音乐天赋和语言上的反讽特质,如何以从未有过的不露声色的方式融入他的画作;以及,他如何像他自己所说“将能量与反能量同时包含在自身中”,以至为可见者附加上一层稀薄、却能够被神秘领会到的不可见者。
目前正在UCCA呈现的“现代主义漫步: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”,涵盖了三十余件保罗·克利的精彩作品,其创作年代横跨他在包豪斯任教的时期,比如以画布上的抽象方块模拟乐曲节奏韵律的画作《方格抽象色彩和声与朱红色重音》(1924)和以飘忽不定的线条破坏建筑立体结构的《黄 / 红 / 棕色小城堡》(1922)。以此为契机,UCCA公共实践部邀请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周诗岩带来“寓言的赋格:保罗·克利与包豪斯”主题讲座,探讨保罗·克利作为艺术创作者与教育者的双重身份,以期为观众呈现二者的互文关系。活动由UCCA公共实践部助理策划人王佑佑主持。
活动日程
13:30-14:00 观众签到
14:00-15:00 主题讲座
15:00-15:30 圆桌对谈
15:30-16:00 观众问答
关于嘉宾
周诗岩(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)
艺术史与先锋派理论学者,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研究兴趣集中在图像研究、媒介理论与文化批判的交叉领域,尤为关注现代性条件下的美学先锋派理论与实践,著有《建筑物与像》《包豪斯悖论:先锋派的临界点》,译著有《奥斯卡·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》《包豪斯剧场》,与王家浩联合主编“重访包豪斯”丛书,该丛书目前已出版10种与美学先锋派相关的基础文献和当代研究专著。
合作方
巴可激光,为您做“睛”彩影像艺术呈现